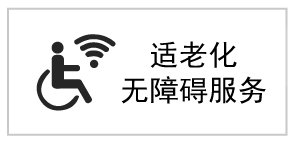释放改革红利 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奠基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责、权、利关系,调动两个积极性,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是迄今为止最适应国情、最适宜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财政体制安排。”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说,1994年以来,我国能够走出一条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轨迹、财政收入能够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方之间你追我赶、竞相迸发的竞争力。
分税制改革改变了财政“包干制”形成的财政分配格局,通过财权与事权的统一划分从制度层面上规范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建立了稳定的激励机制,对引导地方政府行为进而促进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伴随分税制改革,确立了与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模式相适应的分级预算管理体制框架,这对于维护地方财政平稳、规范、透明运行意义重大,也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奠定了基础。
由“分钱”转向“分税”
分税制改革对于地方政府的行为和地方经济发展产生了哪些深刻影响?答案或许可以从分税制与我国农村改革思想路线的比较分析中探寻。
1978年,我国农村改革前后发生的最大变化是由“分钱”“分物”转为“分地”。“分田到户”后,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推动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
“1994年,我国决定以分税制取代‘财政大包干’,其中有借鉴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财政管理体制经验的考虑,但是,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要素,二者有着共同的思想来源和近似的行动路线。”高培勇认为,正是在由“分钱”转向“分税”的基础上,才有了相对稳定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格局,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才得以充分发挥。
具体而言,分税制改革明确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以及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并同步配套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等改革举措,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原则逐步规范税制。
同时,分税制改革明确地方独立享有一定税种收入的基础上,赋予其相应的税收征管权力,这对地方政府产生了巨大的财政激励作用,充分调动起地方的征管积极性。
“在改革顺利推进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1994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是好的。根据初步统计,国家财政收入5181.75亿元,完成预算的108.9%,比上年增长19.2%。”1995年3月,时任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在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指出,财政收入大幅度超过预算,原因之一是实行分税制较好地处理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了各地加强税收征管、努力增加收入的积极性,地方税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都有较大幅度增长。
正如农村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分税制改革明确地方政府能够从本地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成效也立竿见影。
——1994年,广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为298.7亿元,随后持续高速增长,2023年达到13851.3亿元。与此同时,广东地区生产总值(GDP)从1994年的4619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13.5万亿元。
——江西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1993年的65.7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3059.6亿元,年均增长13.7%。其中,税收收入占比总体稳定在70%左右。
——2023年,宁夏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500亿元,达到502.3亿元,与1994年的7.2亿元相比,增长近70倍,年均增速达到15.8%。2023年,宁夏GDP达到5315亿元,与1994年的134亿元相比,增长近40倍。
“通过改变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机制,促使地方政府更加关注地区长期税源建设和经济发展,对推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旭红说。
据统计,我国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1994年的2311.6亿元,增至2023年的11.72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达14.5%。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不断创造新纪录——1994年,我国GDP总量达4.86万亿元,同比增速达13%,且一直到2015年都保持了7%以上的中高增速。
“分税制重塑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激励机制。”中央财经大学教授、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姚东旻说,不再实行包干制财政收入管理体制,按照税种划分收入,也就是用按照税种属性划分财政收入取代了按所有制、企业隶属关系划分,促使地方政府将更多精力用于发展经济,极大地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改革向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方向推进
回顾我国财政发展史,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围绕着地方政府预算是否构成一级独立的预算主体这一核心问题,先后实行了统收统支、统一领导的集中制,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包干制”,直至1994年确定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1994年以后,各地也比照中央对省的分税制框架,在进一步明晰省以下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陆续实行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至此,我国初步形成了涵盖五级政府预算、有中国特色的多级预算体制,这是与市场经济体制、公共财政模式相适应的预算管理体制。
就实质而言,分税制预算管理体制是指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按税种划分预算收入以确定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预算分配关系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
“分税制明确了各级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范围,强化了地方财政的预算约束,提高了地方坚持财政平衡、注重收支管理的主动性和自主性,财政资金筹集和分配更为规范。”李旭红说。
此前实施的“财政大包干”制度,属于较为粗放的财政管理体制。由于地方与中央的财政分配协议“一年一定”,缺乏长远规划,导致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同时,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财权常常面临“支出责任重而财力不足”的困境,难以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必要的投入。
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列为中央预算支出,地方相应列为收入;地方财政对中央的上解列为地方预算支出,中央相应列为收入,中央与地方财政之间都不得互相挤占收入,由此确保财政资金流动的透明度和规范性,从而促进了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
同时,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的规范性得到强化。随着1994年预算法颁布,预算管理进一步实现有法可依。此外,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改革有序推进,有效地提高了预算执行水平,实现了公共支出的全程监督。
“地方政府须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匹配、法定程序和标准编制预算,确保预算的合理性和合规性。同时,须严格按照批准预算执行,通过建立健全预算监督机制,对预算执行的合法性与效率进行监督,有利于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减少职责不清带来的资源配置低效,进而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李旭红说。
而这也恰恰对应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和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日益明显,各级财政支出的重点也逐步由偏重经济建设转向公共事业和服务领域。
“搞市场经济,就要搞公共财政。”高培勇认为,“过去数十年,包括分税制改革在内,我国在财政税收领域所推出的改革举措,实际上都可以归入公共财政这条主线,是以公共财政的建设为取向的。”
改革发展的脚步不能停歇。2013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开始从建立公共财政体制转向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可以说,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建立及以后的调整完善、稳健运行,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要求,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现代财政制度框架基本确立。